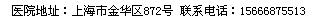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克罗恩病 > 疾病探寻 > 中国炎症性肠病研究现状和进展
中国炎症性肠病研究现状和进展
中国炎症性肠病研究现状和进展
钱家鸣(医院)杨红
中华消化杂志,,36(07):-.DOI:10./cma.j.issn.-..07.
以下内容和版式版权归属中华医学会,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IBD曾被认为是"西方人疾病",近年来其发病在我国和亚洲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近20年,我国IBD病例数迅速增加[1]。我国IBD发病经历了从罕见到多见疾病的演变过程。
1一、中国认识IBD历程回顾中国认识UC较西方国家晚余年。早在18世纪,西方国家即开始认识UC,年英国SamulWilks医师首次将其命名为UC[2]。而我国学者文士域等[3]在年报道了23例UC病例特点之后,经历20余年,在第1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年)中提出了对该病的诊断标准。20世纪80年代,医院分别就UC内镜诊断、药物治疗、并发症和动物模型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阐述了中国UC疾病人群的临床特点。截至年,国内文献报道UC已达2万例[4]。
20世纪20年代末,Crohn医师对与UC类似的一类疾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进行了总结,后期命名为CD(曾用名为克隆氏病)[2]。中国较早的CD文献仍是文士域等[5]在年发表的1例胃、十二指肠和空肠CD的病例报告。由于当时我国肠结核发病率较高,而CD堪称罕见疾病且与肠结核鉴别诊断困难,故很长时间国际上并不承认中国有CD病例。据记载,英国著名病理学家、IBD专家B.C.Morson于年前来医院交流,曾提出在中国和印度这些结核病流行的亚洲国家尚未发现1例真正的CD[4]。然而在进一步的学术交流中,通过对中国CD病例病理标本的认真核对,肯定了中国存在CD这类疾病。同期,刘彤华、潘国宗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CD和肠结核的鉴别标准的相关文章。
随着对IBD认识的深入和临床迫切需求,以年6月的全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为起点,提出了中国UC和CD较为详细的诊断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之后成立了全国IBD协作组、全国IBD学组,中国的IBD研究进入发展阶段,2年提出IBD规范诊治建议[6],年和年分别修订了IBD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7,8]。随后IBD学组分别围绕生物制剂、营养支持、机会感染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这些意见的发布和推广也极大地规范和提高了我国IBD的临床诊治水平。
2二、中国IBD临床流行病学趋势总体而言,中国IBD发病率低,并缺乏疾病管理系统,难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因此,之前中国的IBD流行病学调查资料都是基于住院病例和临床分析的报道。其中年Jiang和Cui[9]分析了年至年国内文献报道的例UC患者,发现10年间病例数上升了3.08倍。年中国IBD协作组对年至年IBD住院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共收集3例UC和例CD患者资料,结果亦显示我国IBD住院患者数呈逐渐增加趋势。
年至年,我国分别在北方城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南方城市广东省中山市、中部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开展了以普通人群为基础的IBD流行病调查[10,11,12],结果显示大庆市IBD、UC、CD标准化后发病率分别为1.77/10万(95%CI1.16/10万~2.59/10万)、1.64/10万(95%CI1.06/10万~2.43/10万)和0.13/10万(95%CI0.02/10万~0.47/10万),中山市分别为3.14/10万(95%CI3.10/10万~3.16/10万)、2.05/10万和1.09/10万,武汉市分别为1.96/10万(95%CI1.62/10万~2.30/10万)、1.45/10万(95%CI1.16/10万~1.75/10万)和0.51(95%CI0.33/10万~0.68/10万)。虽然这些资料的收集存在一定偏倚,但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较为准确的发病率调查。
关于危险因素调查,中国一项较大样本病例对照研究入组例UC患者和名对照者(无消化系统疾病并暴露在相似环境因素下的同事、邻居、朋友),结果显示IBD家族史、感染性肠病为UC危险因素,吸烟、饮茶、母乳喂养为UC保护因素[13]。年在亚太地区进行的一项IBD流行病学调查共纳入例IBD患者(例CD,例UC;其中例为亚洲人)和名健康对照者,结果显示母乳喂养12个月、抗生素、养宠物狗、饮茶和体育锻炼可降低CD的危险因素;母乳喂养12个月、抗生素、饮茶、咖啡、热水浴和儿童时期使用冲水马桶是UC的保护因素,但戒烟是UC的危险因素[14]。
当然,尚需多中心、多地域、多种族临床研究探讨我国疾病人群重要的危险因素,以利于宣传教育和预防。由于我国的IBD流行病学研究刚起步,故疾病预防工作仍任重道远。
3三、IBD诊断的认识和进展1血清标志物:由于早期对于IBD的认识不足和我国结核病高发,IBD误诊率和漏诊率较高,Mta分析显示UC与CD误诊率分别为27.5%和36.8%,而漏诊率分别为32.1%和60.9%,因此精准而及时的诊断是不懈努力的目标。
但是近年欧美提出的一些血清标志物在中国似乎并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如在一些国内入组病例数较多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utrophilcytoplasmicantibodis,ANCA)对UC诊断敏感度在37.9%~56.7%,抗酿酒酵母细胞抗体(anti-Saccharomycscrvisia,ASCA)对CD诊断敏感度为45.2%~65.5%[15,16],其敏感性均较欧美研究[17,18,19](ANCA为60%~80%,ASCA为55%~65%)偏低。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种族差异有关,提示东西方IBD发病机制之间可能存在不同。这也给我国的IBD基础科学研究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机遇,应该着眼于研发我国疾病人群的血清标志物,才会最终寻找到有利于我国疾病人群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指标。
如何与肠结核进行鉴别诊断是IBD诊断的另一挑战。两者之间临床表现相似,且肠镜表现和病理均不容易鉴别。国内Li等[20]率先报道了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鉴别诊断肠结核和CD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4.2%和75.4%,提示该方法可以作为有价值的鉴别诊断CD和肠结核的指标。
2影像学诊断价值:影像学在IBD诊断和随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与内镜具有不同的优势,如计算机断层扫描小肠造影(白癜风遗传北京白癜风医院有哪些那个好